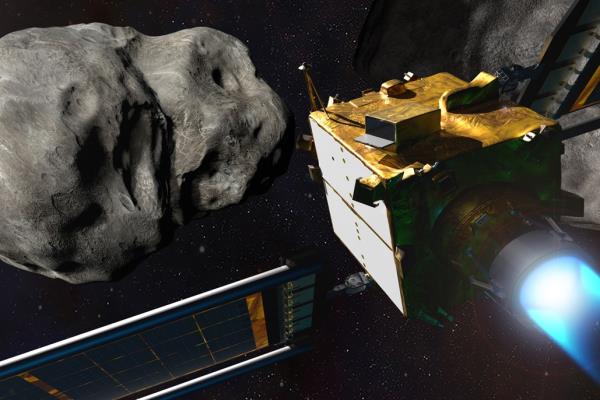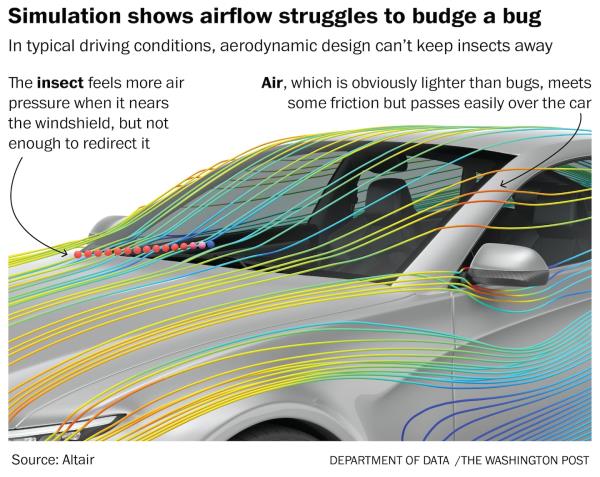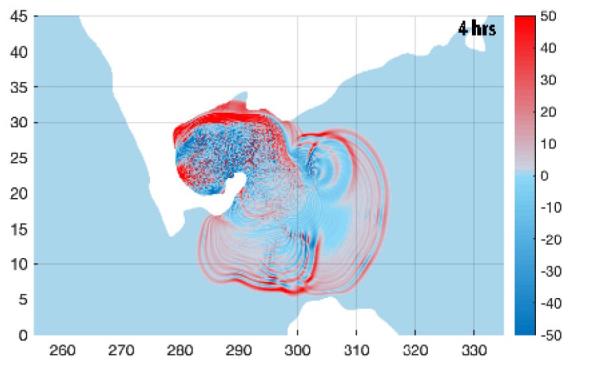当鲁本·加勒戈在伊拉克时,他以解决问题著称。
想想打鼾的海军陆战队员的例子吧——乔纳森·格兰特下士过去常常用锯木材的巨大声音让营房的人保持清醒。格兰特曾告诉他的战友们,如果他们在太吵的时候叫醒他,他并不介意,但从床上爬起来把他摇醒似乎是一件苦差事。
“所以,”加乐高的朋友、部队成员约翰·拜伦(John Bailon)说,“鲁本在格兰特的脚上系了一根绳子,每当他开始打鼾时,他就猛拉一下。它非常有效!”
格兰特是单位里每个人的朋友——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以他似乎无穷无尽的糖果储存而闻名,他很高兴与人分享。但他是加乐高最好的朋友。格兰特曾是加乐高的非正式教练,当他们都在美国时,他帮助加乐高减肥并通过了体能测试。在出征前,加乐高抱着格兰特的孩子,并向他的妻子保证在伊拉克照顾他。2005年5月11日,格兰特的两栖突击车撞上了一个简易爆炸装置。加乐高当时正在附近的一辆车里,他从一名海军陆战队员那里得知格兰特死亡的消息时,他正在一个伊拉克家庭的家中避难。
加乐高觉得自己的胸膛被悲伤撕裂了。
当加乐高回到家中时,他在伊拉克的创伤后压力改变了他的生活。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让他反复做噩梦,经常是关于他所在连队的海军陆战队员——有22人在他执行任务期间阵亡。这有时会导致他酗酒和过度吸烟。这给他的婚姻带来了压力,最终以离婚告终。这让他容易出现他所谓的“极端情绪爆发”。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让他成为了国会议员。
加乐高在国会山的办公室接受采访时说:“我对人为的成功点上瘾了。”“就像能够跑这个或跑那个。”
加勒戈在参战前雄心勃勃,但在参战后,他开始全速前进:作为特工进入政界,在亚利桑那州众议院赢得了一个席位,并于2015年前往华盛顿,在美国众议院代表凤凰城地区。
他的成功是一面盾牌——一种向自己和他人证明他做得很好的方式,一种让他没有时间胡思乱想的方式。“我总是努力让自己忙起来,”他说。
在国会,想要继续攀升的渴望似乎从未消退过。在两届任期内,加乐高曾考虑在2019年竞选参议员(他退出的部分原因是,他的民调数字落后于他潜在的民主党初选对手、宇航员马克·凯利)。在拜登总统任期的第一年,加乐高游说(未成功)担任海军部长。现在,他再次让自己忙碌起来,开始竞选参议员克里斯滕·西内马(Kyrsten Sinema)目前占据的参议院席位。
加乐高被收养的亚利桑那州最近成为了美国一些最疯狂的政治活动的中心:“网络忍者”在不存在的地方寻找选举舞弊;一名牙医出身的国会议员,因为发布了一幅谋杀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的漫画而被剥夺了委员会的职务;Kari Lake是MAGA名人,她仍然拒绝承认自己在2022年州长竞选中失败。加乐高是第一个参加这场将在近两年后举行的竞选的人,但他很可能与莱克和西内马竞争。西内马是一名企业民主党人,后来转为独立人士,她在过去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阻碍她所在的前政党的立法议程。
为了脱颖而出,加乐高花了很多时间谈论进步政治,希望提高最低工资,降低处方药成本。
但加乐高也把心理健康作为他竞选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是他自己的。
他说:“我可以证明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就像这些愤怒的火球,随时都可能爆炸。”“或者恰恰相反,我们就像这些每天晚上都会哭的温顺的人。”
传统上,政客们在谋求更高职位时都会避免讨论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任何对历史有基本了解的国会议员都知道已故副总统候选人托马斯·伊格尔顿(Thomas Eagleton),他是密苏里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以及他如何在1972年因使用电击疗法治疗抑郁症的经历被爆出后被民主党淘汰。加乐高说,他担心被定义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候选人”。
撇开心理健康问题不谈,选民们可以期待听到很多关于加乐高的气质——一个好斗的政治家,那种说话和推特上都是四个字母的词,并受到了MSNBC的长期邀请。加乐高的对手肯定会试图把他描绘成一个象征性的投掷炸弹者,如果不是字面上的投掷炸弹者的话。
他说,他已经注意到在“右翼推特用户”中形成了一个故事线,把他说成是一个“愤怒的”候选人——一种“委婉地说我是一个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不稳定的人,却没有说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部分”。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专家沙利·贾恩(Shaili Jain)说:“我不认为20年前你会有一个公务员对心理健康诊断如此坦率。”
但是,加利西亚人打赌,选民对心理健康有更好、更细致的了解比他们过去可能有斗争——小程度上归因于公众人物,像参议员约翰Fetterman桑)。他的办公室最近宣布他进入住院照顾抑郁沃尔特里德医疗中心和杰森·肯德尔,前民主党冉冉升起的新星,放弃了一个潜在的竞选总统处理自己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在阿富汗服役。
贾森·坎德尔说:“美国人开始理解和信任那些处理好自己问题的领导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东西。”
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混乱的总统任期四年、全球大流行的三年、关于图书馆应该放什么书的尖叫比赛以及美国民主之座的一场起义之后,选民们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拥有更多的“东西”。
通过这种方式,候选人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可能不像以前那样是一种负担。
它甚至可以引起共鸣。
加乐高在芝加哥长大。他母亲是个秘书,父亲是个“混蛋”。
为了养家糊口,老加乐高在建筑工地工作,但回家时经常处于被虐待的状态。身体上的问题,加乐高说他能处理好,但情感上的问题——取笑他读书,称他吃东西的方式是“同性恋”——从那时起就一直困扰着他。
加乐高七年级时,父母分居,父亲也离开了这个家。这是一种解脱,但却造成了经济上的困难,最终加乐高和他的母亲以及三个姐妹搬进了芝加哥南部的一套两居室小公寓。加乐高睡在客厅的地板上。他上大学前都没有自己的床。
加乐高高中毕业后曾考虑过加入海军陆战队,部分原因是他想为国效力,但也因为这似乎是一种肯定能拿到薪水的方式。但他的成绩足够好,为他赢得了哈佛大学的奖学金,他母亲说他不能拒绝这所学校。他在剑桥的一家夜总会当保镖,在校园里打扫厕所,偶尔还会为学生活动提供服务。
“我曾经在政治学院(Institute of Politics)的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的小政治俱乐部里斟酒,”他说。“我讨厌他们所有人。”
这是一个艰难的调整,作为一个穷人的孩子在一个富人的学校,加乐高的学习成绩变得如此糟糕,他被要求“暂停”入学。在此期间,他加入了海军陆战队,并在第二年回到了哈佛。他开始和一位名叫凯特·威德兰的年轻女子约会,她在一次社交俱乐部慈善拍卖会上出价22美元买下了他,并于2004年毕业。
2005年,他乘船前往伊拉克。
拜伦说:“他来我们单位报到,有小道消息说有个海军陆战队员上过哈佛。”“这是反常现象。我们就想,我们一定要见见这个人。”
拜隆对加乐高的第一印象是:他个子不高,是个热情、直言不讳的民主党人。
“这激怒了一些人,”他说。“看起来很有趣。”
加乐高在“琐碎游戏”(Trivial Pursuit)中有击败所有垒手的习惯,但他并不是“哈佛毕业生的典型形象”,该小组的火力队长安迪·布里顿(Andy Britten)说。他是干粗活的,接到要求时总能再带“100发或200发”弹药,“而且他从不抱怨。”
他在其他方面也受到同事们的喜爱,包括领导了一次成功的走私行动,他的女朋友在爱心包裹里装满了掏空的毛绒动物标本,里面装着瓶子里的酒。这就是著名的“泰迪熊行动”。
加乐高很容易交到朋友,但他们成为家人却很困难。一起在战场上——无尽的无聊时光,恐怖时刻,互相保护的行为——足以让他们感觉像兄弟一样。加乐高能让人开怀大笑,这一点也很有帮助。
克里斯·福克斯回忆起有一次他和加乐高被困在沙尘暴中,看不到前方25码以外的地方,但不断听到遥控简易爆炸装置的声音。场面非常紧张,加乐高用他的“黑色军事幽默”缓解了这种紧张。
“他会说,‘我希望下一个爆炸发生在你这边,’”福克斯说。
布里顿说,他和加乐高有一次在被火箭推进榴弹击中后一起跳进了沟里。
“我们只是面面相觑,笑了起来,”他说。“考虑到当时的情况,知道我们必须做什么,躺在伊拉克的沟里,这只是一种轻率。”
交火结束后,他们收集了一把炮弹,布里顿说他今天还留着这些炮弹。
他说:“我敢打赌,他的心也还在。”(Gallego证实了这一点)。
这些贝壳是布里顿幸存时留下的纪念品,但他说他也带着很多他亲眼目睹的死亡。他们的营——包括加乐高的连和另外两个连——损失了48人,这是自1983年贝鲁特爆炸案以来单个海军陆战队营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PTSD是有道理的,”班长安迪·泰勒(Andy Taylor)说。“考虑到我们所经历的一切。”
加乐高回到家中,尽他最大的努力继续他中断的生活。他和凯特住在一起,他们俩搬到了亚利桑那州。他们于2010年结婚。
加乐高在情感上很挣扎,但在事业上很成功。他认为这意味着他不会真的有问题。坚强的外表是如此令人信服,以至于拜伦会问加乐高,他是如何在承担战争负担的同时取得如此成功的。
“我只是把它塞得很深,”他回忆加乐高说,“但当它出现时,它是原来的十倍。”
2016年,凯特怀孕了。他说,作为国会议员和准爸爸的压力,加上焦虑、喜怒无常、幸存者的内疚和不断争取成功的努力,让加乐高无法承受。
“我在这里追什么?”据加乐高的回忆录记载,他在一次心理治疗中这样问自己。答案是:“一个活着的理由。”因为我觉得我不配。”
他说,自从战争以来,他已经很难与人亲近,因为他害怕他最爱的人会被带走,就像他们在战争中一样。现在,他不能再对这段关系做出承诺。
他们在凯特怀孕时分手了。
***
最近的一个星期三,加勒戈在雷伯恩众议院办公大楼的大厅里快步走,以便准时参加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在正常情况下,该委员会的首要任务包括监督地质调查、国际渔业协定和历史战场。但是,由于现在不是正常时期,在委员会将注意力转向1872年的《采矿法》(Mining Law of 1872)之前,成员们需要讨论是否允许他们在武装的情况下这样做。
“有多少成员认为他们需要携带武器参加我们委员会的听证会?”加州民主党众议员贾里德·霍夫曼(Jared Huffman)在提出枪支禁令后问道。
一些人举手,其中包括新上任的共和党众议员安娜·宝琳娜·卢娜(Anna Paulina Luna,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人),她戴着一枚类似半自动步枪的领针,还有共和党众议员劳伦·博伯特(Lauren Boebert,科罗拉多州共和党人),她曾经开过一家名为“射手烧烤”(Shooters Grill)的枪支主题餐厅。
“我觉得我在这里到处都需要一个,”博伯特说。
“想必那些是上膛的武器吧?”霍夫曼问。
“不是没上膛的武器!”Boebert嘲笑。
“你认为我们会伤害你吗?”卢娜随后插话。“我们永远不会伤害你。我会用我的枪保护你。我只是想说清楚。”
“只是对霍夫曼先生澄清一点,”该委员会副主席、科罗拉多州共和党众议员道格·兰伯恩(Doug Lamborn)在轮到他发言时提出。“我之前没有举手是因为我不参与,我不去那里,所以不要把我没有回应解读为任何东西。我想让坏人一直猜下去。”
博伯特指出,世界上有“精神错乱”的人,有很多政治暴力的例子可以作为警示:有一次,一名精神错乱的枪手在国会共和党人参加的棒球训练中开枪;1954年波多黎各民族主义者对国会大厦的袭击。博伯特说话时,加勒戈把手放在下巴上,扬起眉毛。
加乐高说:“来自科罗拉多州的议员忘记提到1月6日,这也是对众议员的攻击。”
“是的,阿什莉·巴比特(Ashli Babbitt)被谋杀的时候真是太可怕了,”博伯特打断了他的话,他指的是一名妇女在试图从破碎的窗户爬进议长大厅时被国会警察开枪打死。
加乐高那天在众议院,站在椅子上,帮助他的同事戴上防毒面具。在解决问题的模式下,他制定了一个计划,如果他不得不战斗,他就把夹克口袋里的钢笔当刀用。(他说,“如果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会刺伤别人的眼睛,拿走他们所有的武器。”)后来,他就如何应对与叛乱有关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向国会议员提供了建议。
这种状况已经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他仍然会想起他打鼾的朋友格兰特,在他死后,他只能去看望他的妻子一次,因为太痛苦了。
加乐高在回忆录中写道:“让他死,我感到内疚。”“我告诉她我会照顾他。”
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加乐高在车队中一直坐在格兰特旁边,他不可能摆脱这样一种感觉:他本可以和他的朋友一起死,甚至可能代替他死。
“死的应该是我,”他写道。“我永远不会超越这个事实。”
格兰特有家庭,加乐高未婚。他无法超越这个事实,但也许他可以学着接受它。到起义发生时,加乐高已经做了多年的治疗工作,致力于自己和他的沟通技巧。公开谈论他的挣扎对他有所帮助。有些事实已经改变了。他和前妻凯特一起抚养了一个儿子,凯特现在是凤凰城的市长。他也开始了一段新的感情。2020年,他向民主党游说者西德尼·巴伦(Sydney Barron)求婚。他更善于和她交流自己的感受。2021年,他们结婚了,今年晚些时候他们将迎来第一个孩子。
正因为如此,当他的同事问他如何处理与起义有关的创伤时,加乐高觉得他实际上可以给出一些好的建议。
“有些建议很简单,”他说。“多喝水。锻炼。四处走走。”
而且,如果步行还不够,他们还可以以加乐高为榜样,寻找新的跑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