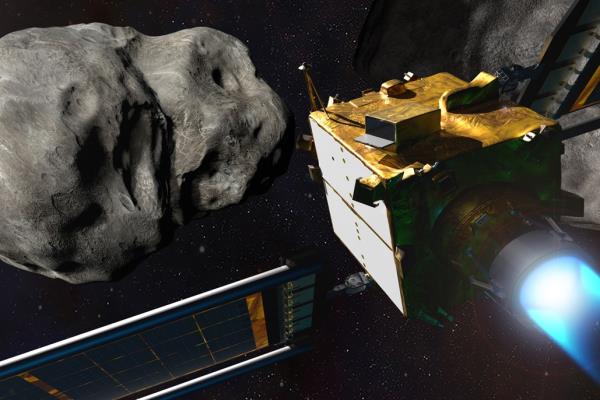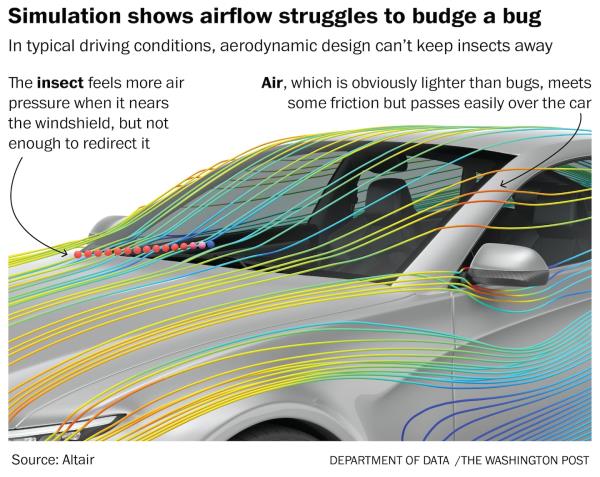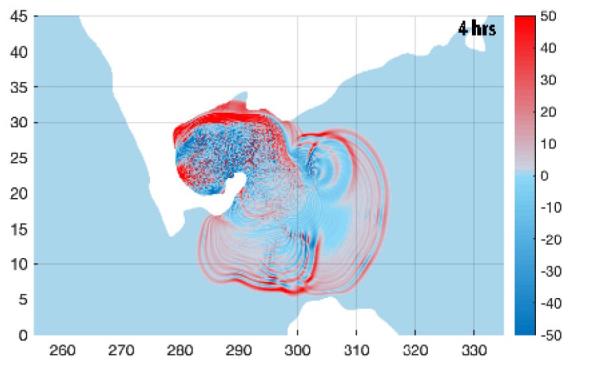公诉人站在陪审团面前,请他们考虑一下缺失意味着什么。
美国助理检察官vinsamut Bryant说,失踪是指你把钱包放错了地方。当你把它放错抽屉或口袋的时候。但如果有人偷了你的钱包——如果他们恶意拿走了你的钱包——那就不算丢了。这是一种更黑暗的东西,是一种永恒的东西。
陪审团是在那天早上被请来审理一起谋杀案的。这是一起没有尸体的凶杀案,一开始被归类为失踪人口而不是死亡。并没有什么忏悔。没有血。没有武器。没有证人。搜救犬没有发现任何活人的气味,寻尸犬也没有发现任何腐烂的气味。这起涉嫌谋杀的案件十多年来一直没有侦破,旁观者不无理由地怀疑,此案是否就是侦破不了。
当时的问题是,13年前,一个名叫艾萨克·莫耶的男人是否谋杀了一个名叫Unique Harris的女人。这次审判是为了最终结束这个折磨她的家人,也让包括我在内的陌生人感到困惑的谜团。
我从一开始就跟踪这个案子。我在其他记者之前写过这篇文章。我一直在独特失踪的特殊情况下寻找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有时会在半夜醒来,在网上搜索是否有任何解决方案。
在试验结束时,我意识到我理解错了。
回到2010年秋天。Unique Harris是一位24岁的母亲,她最近和两个儿子的父亲在里士满分手,搬到了华盛顿特区,为了离家人更近一些。她还在新租住的房子里安顿下来,尽管里面的箱子已经拆了一半,但还是很整洁。她给表姐蒂芙尼(Tiffannee)打了个电话,有了一个主意。蒂芙尼9岁的女儿塔拉亚(Talaya)生日快到了,Unique希望她的生日礼物是在她家过夜。对塔拉娅来说,这是一个了解她的表兄弟、独一的儿子的机会,他们一个5岁,一个4岁。
蒂芙尼和塔拉亚会讲述他们在审判那天晚上的记忆:10月9日晚上,蒂芙尼送女儿回家,几个小时后打电话给她。那时,这对表兄弟已经开始吃爆米花,开始看一部电影,但当电影比她预期的更粗俗时,Unique最终让他们关掉了这部电影。九点半左右,她把三个孩子塞进卧室,然后在客厅安顿下来,那里是她自己睡觉的地方。
那天晚上,塔拉娅醒了一次,好像听到独一在跟什么人打电话,然后又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七点半左右,当她和两个男孩起床时,独一不在客厅,也不在公寓的其他任何地方。
塔拉娅立刻打电话给妈妈,说她找不到独一了。蒂芙尼并不担心。她猜想独一是冲到街角的商店买了一加仑牛奶当早餐。尽管如此,她还是出发去了独一的公寓,由于地铁公司周末的公交车时刻表不固定,这趟旅行花了她近两个小时。
当她到达时,她惊恐地得知独一还没有回来,她开始搜查公寓。独一的手机不见了。但是冰箱里装满了食物——没有必要去街角的商店——而且无论如何,Unique也不可能支付杂货的费用,因为她的钱包和钱包还在公寓里。她的眼镜也是。
这副眼镜让蒂芙尼的惊慌变成了恐慌,她给尤尼特的母亲瓦伦西亚打了电话。独一视力很差,而且她没有隐形眼镜。她去夜总会时戴着眼镜。她和约会对象吻别的时候戴着。她醒着的每一分钟都戴着眼镜,睡觉的时候,她不是把眼镜放在床头柜上,而是放在床上,放在离脸几英寸远的枕头上,这样她甚至可以在睁开眼睛之前就抓住眼镜。
瓦伦西亚知道独一不带钱包离开会很奇怪。
她知道独一不带眼镜是不可能离开的。
将近一年后的2011年,我是一名年轻的特稿作家,正在寻找一篇报道。当时我的专长是在截止日期前写一些有趣的文章,我告诉一位编辑,我想要一些更有实质内容的东西。一些能引起情感共鸣的东西,一些让人觉得很重要的东西。
我不记得是谁的主意搜索华盛顿的失踪人口数据库,但我记得当我开始搜索的时候只有一个案子有明显的时效性,那就是Unique的案子。下个月是她失踪一周年。
当我联系瓦伦西亚·哈里斯时,我不确定她是否愿意接受媒体对她女儿失踪的更多关注。但事实证明,从一开始就没有多少媒体关注。Unique是一位住在华盛顿东南部一个贫困社区的工薪阶层黑人妇女。她不符合那种金发、中上阶层、以南希·格蕾丝为诱饵的失踪人口模型。瓦伦西亚一直在自己发传单,试图自己找到嫌疑人,自己催促警察,挨家挨户敲门。她一直在乞求有人,任何人,关注她女儿的失踪。
当我打电话给瓦伦西亚的时候,她敞开了自己的生活。当然了。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但对她的大女儿却很温柔。她之所以选择“独一无二”这个名字,是因为瓦伦西亚认为她就是这个名字——世界上最特别的孩子。瓦伦西亚告诉我,当尤尼特还在蹒跚学步的时候,她的鞋子一直洁白无瑕,因为瓦伦西亚从来没有放下过她。
瓦伦西亚把我介绍给了独一的祖父,在她失踪后的几天里,他曾冷酷地爬进独一公寓大楼的垃圾箱里,以确保她没有被放在那里。致独一的哥哥,他一直想陪伴失踪妹妹的儿子们。尤尼特的儿子们,自从他们的母亲离开后,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蹒跚学步的痕迹,长成了苗条的小男孩。
她的家人尝试,一次又一次,拼凑出独特的十几小时会发生什么当她把孩子睡觉和醒来时发现她失踪的时间跨度,它后来成为明显的,更像是四或五个小时,因为独特的电话记录会显示她和她男朋友在电话上交谈时深夜,完成后调用在早上三点。
在那四五个小时里,她消失了。她就这样消失了。
任何了解真实犯罪的人都知道,这种类型的小说是由奇怪的案件推动的。深不可测的阴谋,对不可能的事情的痴迷。如果尤尼特的失踪看起来很常见,我不知道我还会写她的故事:如果她是一个风流的丈夫,最终决定和他的情妇重新开始,或者是一个瘾君子,再找一次芬太尼就再也没有回来。
关键是她的故事并不常见。这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她离开了,为什么只带了手机而没带钱包?如果她被绑架了,为什么没有赎金?如果她是被谋杀的,那尸体在哪里?
这是在“连环”播客或真实犯罪热潮之前,在犯罪纪实剧在Netflix上获得自己的类别之前。但是,就像现在一样,如果你想让一个被忽视的案件浮出水面,那么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一篇长篇报道只会有所帮助。我不想夸大我自己微不足道的参与:瓦伦西亚·哈里斯一直是她女儿火焰的守护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有成就的、不屈不挠的受害者倡导者——不仅是为了她的女儿,也是为了许多黑人女性,她们的故事从未登上黄金时间。瓦伦西亚得到了黑人与失踪基金会的支持和指导,这是一个致力于宣传有色人种失踪事件的组织。
但我希望,至少,我为瓦伦西亚想要的、Unique应得的关注做出了一点贡献。
故事发表后不久,我接到一个电视节目的电话,节目内容是悬疑悬案;他们看到了那篇文章,决定做一期关于独一失踪的节目。后来,独一的家人被莫里·波维奇和《早安美国》邀请。Lisa Ling在《我们的美国》(Our America)节目中介绍了这个案子。播客“犯罪瘾君子”(Crime Junkies)最终探讨了“独一”的案子;其他播客紧随其后。
她的命运成为陌生人猜测的话题,他们会在网上发帖或写信给我,告诉我他们认为她发生了什么事。读者们猜测,在塔拉娅失踪的那天晚上,“独一”邀请她到她家过夜,这当然是有意义的。也许这意味着她打算离开,并确保她年幼的孩子不会完全无人看管。没错,她的眼镜被落下了,但那是一副较新的杜嘉班纳(Dolce & Gabbana)名牌镜框。也许"独一"保留了她的旧钢圈戴上了,以逃避调查。
结果是有人用了独一的社会安全号码,但警方调查后发现,这个女人显然不是独一,也和她没有任何联系。
有模糊的传言说,在尤尼卡失踪前几天,她的公寓大楼里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也许,这个理论认为,独一目睹了这一切,然后被她所看到的吓坏了,她在安静的夜晚逃跑,以保护自己免受坏人的伤害,他们可能会试图让她闭嘴。
也许是坏人让她闭嘴了。也许是这样。
2016年10月,华盛顿警方接到线报,称Unique住在乔治亚州的学院公园(College Park)。他的名字是" Lexis "。同月,警方收到线报称独一住在底特律,化名为“好莱坞”。有一次,一个自称通灵的人打电话给我,说她感觉到独一活得好好的,在亚特兰大当服务员。如果警察能查遍亚特兰大的每一家餐厅,肯定能找到"独一"除了等待。转念一想,也许不是亚特兰大,而是大西洋城。
如果被追问,我自己的理论是这样的。“独特”失踪的那天晚上,她刚和男朋友通完电话——他有不在场证明,他不在州——正要准备睡觉时,她决定出去做最后一件事:倒垃圾,抽根烟。她的手机已经在口袋里了,但她没有拿钱包,因为她预计几分钟内就会回来。至于她的眼镜——谁知道呢,也许她确实有第二副。
无论如何,她一走出公寓,就被搭讪了。被拖进车里开走了。
我还以为是连环杀手呢。那时候我看了很多《犯罪心理》我有阴谋论。不管发生了什么,我断定这是一件完全不可预见和奇怪的事情。
当我第一次写Unique的时候,我20多岁,刚结婚,没有孩子。2018年,我从专题作家变成了一名性别专栏作家。我的职位是在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倒台之后设立的,当时编辑们正在寻找一个人来撰写目前作为一名女性意味着什么。
我从来没有写不完的东西。通过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的确认听证会,早该对工作场所性骚扰进行的反思让位于早该对性侵犯进行的反思,后者让位于关于“好人”、同意和整个危险世界的对话。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读者说,她们被伴侣虐待,或被熟人强奸,或被她们不愿上床的男人跟踪。
作为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这通常意味着生活在危险之中。有些人仍然很难看到甚至想象的危险,尽管它很常见。
我仍然时常想起独一。每年10月10日,也就是她失踪的纪念日,我都会想起她。当我成为母亲时,我想起了她。如果我出了什么事,我的恐惧不再集中在我自己的痛苦和折磨上,而是因为我知道这将使我的女儿失去一个妈妈。大家都说独一是一位尽职尽责的母亲,她会独自离开,这种想法开始变得更加荒谬。
2021年,我收到了一位同事发来的电子邮件,主题很神秘:“在一起悬案中被捕。你还记得这个故事吗?”
被捕的男子名叫艾萨克·莫耶。
调查人员对莫耶并不陌生。他在调查初期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独一的孩子们曾向家人提到她有个朋友叫“冰山”;莫耶有时叫冰山。当时,警察正在采访独一认识的每个人,他们还带着莫耶进行了多次谈话。
是的,他们是朋友,他在审讯时为陪审团播放的采访中告诉警方,但他不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他记不起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他说,那不可能是她失踪的那晚,因为他只在白天去过她的公寓。他说,每次他来看她,他都会在天黑前离开,因为她要哄孩子睡觉。
莫耶在一次采访中告诉警方,他们的关系纯粹是柏拉图式的,因为他知道她有男朋友。在另一次采访中,他说他们只是玩玩,但脖子以下的都没有。在一次采访中,他说他们可能发生过性关系,但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又说根本没有任何身体活动。也许她回里士满了,他说,并告诉警方她经常说要搬回弗吉尼亚。
不管警方是否觉得他反复无常的回答有可疑之处——人们在被问及性生活时感到慌乱是很正常的——他们显然觉得他们没有证据或理由指控莫耶犯罪。
但是,在“独一”失踪十多年后,这个案子有了突破。这些突破看起来如此明显,以至于让你怀疑整个调查是否都失败了。
从独一的沙发垫子上采集到的精液的痕迹被上传到国家数据库,并被发现与莫耶相符。一名法医分析人员在庭审中作证说,这枚戒指属于另一名男子的几率不到十亿分之一,也就是1后面加27个0。沙发坐垫的一大块,大约柚子大小,也不见了。“独一”的妹妹作证说,它几天前并没有失踪;检察机关推测,这是因为它含有额外的证据。
精液可能在任何时候被留下,不仅仅是“独一”失踪的那个晚上,但还有一个原因:莫耶的一个前狱友作证说,莫耶曾经告诉他,有一个女孩失踪了,但她永远不会被找到,因为莫耶“做得对”。
"失踪女孩"可能指的是其他人,而不是"独一"但还有这个
原来在Unique失踪的那晚,Moye因为之前的犯罪被假释,他的脚踝上戴着一个GPS监视器。(陪审团不被允许听到是什么事件促使了监控器的出现,我也无法在莫耶的网上法庭记录中找到有关其来源的记录)。无论如何,出于我永远不会完全清楚的原因,侦探们要么没有意识到他戴着那个装置,要么他们认为莫耶没有足够的嫌疑,认为这很重要。一位执法部门的消息人士告诉我,在那个时候,要找出一个不是正式嫌疑人的人是否戴着监控器,可能根本不是正常调查程序的一部分。
最终,调查人员调出了独一失踪当晚监视器的GPS记录。记录显示莫耶离开了他的家,走到她的公寓大楼。他在晚上10点39分到达。他直到第二天早上7点26分才离开。
莫耶没有出庭作证。他的辩护团队辩称,这些证据都是推测性的。那天早上,当莫耶离开独一的公寓时,他穿过一个公园走回家。他怎么能背着125磅重的尸体这么做?如果他在路上把独一的尸体处理掉了,那为什么一直没找到她?“独一”的孩子还小,也许他们搞错了自己醒来的时间,”辩方提出。也许要考虑的时间窗口比任何人意识到的都要长。至于莫耶的前狱友,辩方认为他不值得信任,并指出他的证词不具体,也没有提到Unique。
最重要的是,辩方辩称,整个调查都很草率,莫耶成了那些没有更好答案的侦探们的替罪羊。莫耶的律师承认,Unique身上可能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但他们的客户“与此无关”。
检察官布莱恩特辩称,证据已经足够清楚了。除了脚踝监视器上的数据、沙发上的精液和狱友的证词,她还注意到:
在她失踪前的几天里,Unique和Moye经常通电话。10月9日,他们通了很多次电话——逮捕宣誓书上说,一整天一共打了13个电话——然后莫耶在晚上10点39分又打了一次电话,就在他的脚踝监视器显示他到达她的大楼的时候。检察官表示,这个电话是为了告诉Unique他在楼下,让她让他进去。
但在10月10日早上他的脚踝监视器离开她的家之后,即使他知道人们在寻找Unique,即使他告诉警察她可能还活着,她可能会跑回里士满——即使这样,至少根据法庭上提供的电话记录,Isaac Moye再也没有给Unique打过电话。
布莱恩特和她的同事告诉陪审团的故事是这样的:莫耶来到Unique的公寓期待做爱,因为他们以前可能发生过性行为。但一旦他来了,她就没有兴趣和他上床了。她对他一点也不感兴趣。孩子们都睡着了,独一整夜都在弗吉尼亚乡下和男友帕里斯聊天,为他们的未来制定计划。
控方称,艾萨克·莫耶整晚都在看她打电话,对她不关注他越来越不安。当她最后一次挂断电话时,那通电话在凌晨三点之后才结束,他终于崩溃了。
检方对“独一”失踪之谜的回答非常普遍:一个男人嫉妒了,觉得自己欠了什么,于是惩罚了那个不愿给他东西的女人。
她没有因为目击了一场谋杀而保持沉默。她没有被连环杀手抓走扔进车里。她不叫" Lexis "或" Hollywood "她不是在亚特兰大或大西洋城当服务员。
布莱恩特告诉陪审团,“独特的哈里斯”并没有神秘失踪。“独特的哈里斯”不幸地离开了。
在得知莫耶被捕的消息后,我一直在想我是怎么错的。有多少人在猜测独一失踪和可能死亡的意义时错了。在假设不可能的故事。
在审判期间,我发现自己想的不再是她失踪时的情况,而更多的是她的生活情况——那些在证人席上由朋友和家人讲述的零碎信息。
当Unique搬离Richmond时,她儿子的父亲欠了她数千美元的抚养费。在等待即将到来的法庭日期的同时,她依靠SNAP的福利勉强度日,她希望法庭会下令让他付款。在她失踪后,在一段为陪审团播放的视频片段中,他告诉警方,他是无辜的,没有造成她的失踪,但他承认,在他们打架的时候,他打了Unique几次。
当她离开他搬回华盛顿时,她开始尝试过新的生活,认识新的人。她遇到了公寓大楼的维修工,他多年前被判犯有重罪谋杀罪,居民们认为他令人毛骨悚然,在Unique失踪后不久就被解雇了——艾萨克·莫耶的辩护律师在证人席上向一名侦探证实了这一点——据说他未经允许就进入了居民的家中。
根据一份详细调查她失踪的警方证词,她和一个男人在一起,这个男人有三个前伴侣,他们报告说他曾虐待过她们。
她和Moye一起度过了一段时间,根据法庭记录,Moye在他生命的早期已经承认了与性有关的罪行。
据说有人传染给了她疱疹。她失踪后,在她的浴室里发现了一瓶治疗药物。她的一位朋友在庭审中作证说,Unique没有透露是谁把性病传染给了她,但她确实谈到了这种疾病是如何击垮她的,因为它让她担心亲吻自己的孩子。
她遇到了帕里斯,帕里斯后来成为了她的新男友。帕里斯决心为自己创造一个光明的未来,最近参加了美国劳工部资助的一个在弗吉尼亚农村的住宿就业培训项目。他告诉陪审团,当他去就业中心工作时,他每天晚上都和Unique通电话。当他完成成为一名野外消防员的训练时,他们正考虑搬到一起住。她给他发了一张自己穿着万圣节服装的照片——一只性感的瓢虫,但仍然戴着她的Dolce & Gabanna眼镜——他告诉她,他认为她不应该穿这种服装。不是因为他嫉妒,而是因为他担心暴露的服装会让她成为目标。
在审判期间,这就像晴天霹雳一样击中了我,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个年轻的记者,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独一被潜在的危险包围着。不是因为奇怪的、特殊的情况,而是因为常见的情况。她有经济上的危险,因为她的前夫没有支付孩子的抚养费。她一直处于危险之中,可能来自多名据称虐待其他女性的男子。她的健康因为某人传染给她一种性传播疾病而受到威胁。
她周围可能存在危险,就像我在过去五年中接到电话的那些女性一样,她们对制度和社会辜负她们的方式感到沮丧,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尝试过自己的生活反而会结束自己的生命。
至少从她姐姐艾希礼的证词来看,Unique有一点是不寻常的。这就是独一对别人的信任程度。艾希礼把这归因于独一天生的正派。艾希礼说,独一总是把别人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所以别人要伤害她,这对她来说是不可理解的。
阿什利说,独一在学习上有困难,这让她在学校很困难,但她有很高的情商,人们自然想和她在一起。她是家庭庆祝活动的管理者,她会提前几个月在她挂在墙上的日历上标记每个人的生日。她曾计划报名参加课程,成为一名按摩治疗师或持证护理助理——两者都是帮助人的职业。
在为期三周的审判中,阿什莉是家中唯一一个每天都出席的人。在13年的时间里,她的家人一直在为解决问题祈祷,他们被迫继续前进,即使他们的生活被一个决定性的事件打乱了轨道。独一的祖父爬进了垃圾箱,直到去世都没有发现他的孙女出了什么事。独一的哥哥,他曾试图照顾他的侄子们,现在自己也被关进了监狱。独一的表妹蒂凡妮(Tiffannee)是第一个在女儿的生日过夜派对后发现独一失踪的成年人。她来到法庭作证,离开时泣不成声,想念她最好的朋友,在这么多年之后,她仍然在想,自己是否本可以做些什么来阻止独一的失踪。
阿什利告诉我,瓦伦西亚的家人已经决定,让他上法庭不是个好主意。独一失踪多年后,瓦伦西亚为女儿讨回公道的决心愈发坚定。至少有一名前侦探曾向自己的上司抱怨说,瓦伦西亚就是不肯松口。侦探在审判中承认了这一点——侦探感到沮丧,因为当她负责调查时,瓦伦西亚每天多次联系警察分局,询问他们为她的女儿做了什么。
我原以为阿什利的意思是,为了瓦伦西亚的精神健康着想,她避开这个试验不是个好主意,但她后来澄清说,她的意思是,对这个试验来说,这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令人担心的是,瓦伦西亚最终遇到了据称对她女儿的死亡负有责任的人,她可能会大发雷霆。
在结案陈词的那天,瓦伦西亚终于来了。她穿着一件鲜红色的运动服。她带来了朋友和家人,他们也穿着红色的衣服。她本想穿几年前做的t恤,上面印着Unique的脸和瓦伦西亚的电话号码,但法庭规定不允许公开展示自己的主张。红色一直是“独一”最喜欢的颜色,所以她决定用红色作为秘密展示的颜色。
自从多年前我写过关于她女儿的文章后,我们就再没说过话;我的原则是不和我面试的人保持联系,除非他们先联系我。我从没想过要打扰你。但她几乎立刻就认出了我,即使是在她生命中最激动、最重要的一天,她还是花时间告诉我,十多年前我试图捕捉尤尼特的故事是有意义的,我是“一个真实的人”。
她这么说真是太好了。但我现在想要重新讲述这个故事是有原因的——不仅仅是有了新的证据,还有新的视角。作为一个20多岁的女人,我一直被一个想法所吸引,即未解之谜是诱人的,迷人的。作为一个40多岁的女人,我更容易意识到,这些谜团背后的真相可能只是令人绝望的悲伤。《真实犯罪》关注的是非同寻常的事情。但真正的犯罪是普通的,而且太常见了。
如果不是在2010年10月的一个晚上失踪,Unique Harris今天已经是一位37岁的十几岁孩子的母亲了。
经过整整两天的审议,陪审团宣布他们达成了一致决定:艾萨克·莫耶犯有二级谋杀罪。
瓦伦西亚发出了一声我甚至无法形容的叫声,那是喜悦、解脱和痛苦的确切交汇,然后在法官要求法庭秩序时,几乎是在声音刚从她嘴里出来时就把它咽下去了。
几分钟后,她来到走廊,双膝跪地,感谢上帝正义得到了伸张。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尽可能多地伸张正义。